《南下往事:灰色江湖》中的林炎是很有趣的人物,作为一部都市日常风格小说被痴情九哥描述的非常生动,看的人很过瘾。“痴情九哥”大大已经写了104024字,最新章节第15章。主要讲述了:1998年7月13,下午四点二十分。东莞火车站像个巨大的蜂窝,嗡嗡作响。绿皮火车吐出一团混杂着汗酸味、泡面味和劣质香烟味的人。林炎被裹挟着涌出车厢,蛇皮袋撞在膝盖上——里面是二十斤炒米饼,爷爷非说广东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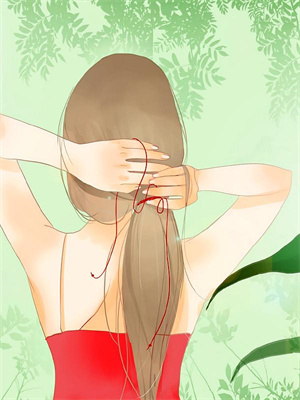
《南下往事:灰色江湖》精彩章节试读
1998年7月13,下午四点二十分。
东莞火车站像个巨大的蜂窝,嗡嗡作响。
绿皮火车吐出一团混杂着汗酸味、泡面味和劣质香烟味的人。林炎被裹挟着涌出车厢,蛇皮袋撞在膝盖上——里面是二十斤炒米饼,爷爷非说广东东西贵,硬塞的。
他站稳,抹了把汗。
183公分的身高在人群里很扎眼。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裤,军绿色跨栏背心下,肌和腹肌的轮廓若隐若现。这不是健身房练出来的,是爷爷从小让他扎马步、挑水、劈柴,十八年山野生活雕琢出的精壮。
裤兜里,二十三块五毛钱被汗浸得发软。
“靓仔,住店不?有电视,一晚十蚊!”瘦男人扯他袖子。
“电子厂招工!月薪五百,包吃住!”另一个举着破纸牌。
林炎摇摇头,攥紧蛇皮袋挤出人群。爷爷的嘱咐在耳边:“到了东莞,先找厚街制衣厂的江叔,他欠我人情……”
话音未落,三个人堵住了出站口的角落。
典型的火车站老鼠。
黄毛,刀疤脸,胖子。呈三角站位,经验老道。
“小子,借点钱吃饭。”黄毛弹掉烟头,露出焦黄的牙。
林炎抱紧袋子:“没有。”
“哟,还挺硬气?”刀疤脸上前就拽蛇皮袋。
就在那只脏手要碰到袋子的瞬间,林炎侧身——动作不快,甚至有些随意,但刀疤脸的手擦着袋子边缘滑了过去,整个人一个踉跄。
爷爷教的:避实就虚,三分让,七分藏。
“妈的!”胖子一脚踹来,直蹬林炎小腹。
这次林炎没躲。
“砰!”
一声闷响。脚结结实实踹在蛇皮袋上,二十斤炒米饼像堵软墙。胖子“嗷”地一声,抱着脚原地跳,脸色煞白。
“!”刀疤脸啐了口唾沫,右手往腰间一摸。
弹出来,刀刃在午后阳光下反着冷光。
五十米外,火车站保安在点烟。三十米外,人涌动,没人往这边看。
林炎深吸一口气。空气里有摩托尾气的呛味,路边摊炒粉的焦香,还有某种淡淡的、像是栀子花的味道。
他想起离家前夜,爷爷在煤油灯下摆弄三枚铜钱。铜钱落在破木桌上,叮当作响。
“阿炎,这次去南方,要是有人你动手。”
老人抬起浑浊的眼睛。
“打太阳,用六分力。”
“为什么是六分?”
“四分是教训,八分是残废,十分是死人。六分,刚好让他躺三天,记得清疼,要不了命。”
刀光刺来。
林炎动了。
不是爷爷教的任何一招一式,是本能——身体左旋,刀锋擦着右肋划过,他能感觉到刀刃切开空气的凉意。左手如电,扣住刀疤脸持刀的手腕,拇指狠狠按住某个位。
“啊!”刀疤脸惨呼,手指一松。
刀还没落地,林炎的右肘已经抬起。
六分力。
“嘭!”
沉闷的撞击声。肘尖精准命中太阳偏下半寸——这是爷爷改过的位置,疼,晕,但不伤脑。
刀疤脸眼白一翻,软软瘫倒。
整个过程不到五秒。
黄毛刚反应过来,林炎已经转身,左手成掌,在他颈侧轻轻一斩——这次是四分力。
黄毛捂着脖子呕,跪倒在地。
胖子还在抱着脚哼哼。
林炎弯腰,捡起。刀柄还残留着汗渍的滑腻。他掂了掂,手腕一甩。
“当啷。”
刀落进五米外的垃圾桶。
他又从兜里摸出三张皱巴巴的一块钱,蹲下身,塞进刀疤脸上衣口袋。
“看医生。”声音平静。
说完提起蛇皮袋,转身要走。
“等、等等——”
声音是女的,带着客家口音的软糯。
林炎回头。
出站口的阴影里,站着个姑娘。碎花衬衫,蓝色牛仔裤,两条麻花辫垂在前。她背着个大编织袋,手里还拎着个帆布包,手指被勒得发白。
黄昏的光斜斜切过来,照在她脸上。
很净的一张脸。眼睛很大,此刻瞪得更圆,睫毛在光里投下细密的影。鼻尖有细密的汗珠,嘴唇因为紧张而微微抿着。
她身后,跟着三个畏畏缩缩的男人——正是刚才那三个混混,现在都低着头,像个鹌鹑。
“他们……”姑娘脸涨得通红,指了指地上瘫着的刀疤脸,“是我老乡。我们一个村的……老家发大水,房子冲垮了,实在没法子才……”
声音越来越小,最后几乎听不见。
林炎没说话。他看着姑娘的眼睛,那里面的慌乱是真的,羞愧也是真的。
远处,火车站钟楼“当当当”敲了六下。钟声在嘈杂的空气里荡开,惊起一群停在电线上的麻雀。
“去哪?”他问。
姑娘愣了愣,才反应过来是问她:“厚、厚街,振兴制衣厂。”
“顺路。”
林炎走过去,提起她手里的帆布包。很沉,估计是衣服被褥。
“哎,不用,我自己……”姑娘想推辞。
他已经转身往公交站走。姑娘咬了咬嘴唇,小跑着跟上。
走出十几米,她小声说:“我、我叫周小雅。周瑜的周,大小的小,文雅的雅。”
“林炎。双木林,两个火的炎。”
“刚才……谢谢你。”周小雅声音更小了,“你功夫真好。”
“爷爷教的。”
沉默。
人声,车声,火车站广播声。空气里摩托车的汽油味越来越浓,路边摊的炒粉在铁板上滋滋作响,还有她身上那股淡淡的、越来越清晰的栀子花香。
公交站挤得像沙丁鱼罐头。
等车的人推搡着,咒骂着。林炎用身体挡在周小雅外侧,蛇皮袋横在身前,隔出一点可怜的空间。
周小雅被挤得几乎贴在他口。
她能闻到他身上汗水混合着某种皂角的味道,不難闻,反而有种山野的净。隔着薄薄的背心,能感觉到他膛的温度,还有下面结实肌肉的轮廓。
脸一下子烧起来。
“车来了!”有人喊。
人群像水一样涌向车门。林炎一手提着两个包,另一手下意识往后一捞,正好揽住周小雅的腰。
纤细,柔软,隔着衬衫能感觉到体温。
周小雅身体一僵。
“上去。”林炎在她耳边说。热气喷在耳廓,她耳瞬间红了。
几乎是半抱半推,两人挤上车。投币箱“哐当哐当”响,司机用粤语骂着什么,车厢里弥漫着汗味、尘土味,还有不知谁带的咸鱼的腥气。
没座位。两人被挤在后门附近的栏杆旁。
周小雅面对车窗,林炎站在她身后,手臂撑在栏杆上,把她圈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小空间里。
车开了,摇摇晃晃。
每一次颠簸,周小雅的后背都会轻轻撞上林炎的膛。第一次,她触电般往前躲。第二次,躲不开。第三次,她咬住嘴唇,手指紧紧抓住栏杆。
第四次,林炎忽然开口。
“你身上很香。”
周小雅浑身一颤。
“是、是栀子花。”她声音发飘,“我们村后山好多,我临走前摘了几朵,夹在衣服里……”
“嗯。”
就一个字。然后又是沉默。
但空气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拥挤的车厢,摇晃的公交车,嘈杂的人声,都成了模糊的背景。只有两人之间那不到一寸的距离,还有空气中越来越浓的、混合着汗水和栀子花的味道。
车过了一座桥。周小雅透过脏兮兮的车窗,看见河两岸密密麻麻的厂房,烟囱冒着白烟,霓虹灯开始一盏盏亮起来。
红的,绿的,黄的。
光晕在渐暗的天色里化开,像打翻的颜料。
“你……吃过饭没?”她忽然问。
林炎摸了摸裤兜。还剩十八块五。
“我请你。”周小雅抢着说,低头在帆布包里翻找,摸出两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。
递过来一个。
油纸揭开,是个白面馒头。馒头表面有些了,但掰开,里面是红糖馅,还温着。
“我自己蒸的。”她小声说,“路上吃。不嫌弃吧?”
林炎接过来,咬了一口。
很甜。红糖的甜混着面粉的香,在舌尖化开。
“好吃。”他说。
周小雅笑了。眼睛弯成月牙,脸颊有两个浅浅的梨涡。
她也掰开自己的馒头,小口小口吃着。偶尔偷偷抬眼,从车窗反光里看身后的男人。
他吃得很认真,一口一口,咀嚼得很慢。喉结随着吞咽上下滑动,下颌线硬朗清晰。
长得……真好看。周小雅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,脸又红了。
车又过了一站。下去几个人,又挤上来更多。有个瘦猴似的男人挤到周小雅身边,眼睛往她口袋里瞟。
林炎忽然伸手,搭在周小雅肩上。
“站稳。”他说。
瘦猴男人对上林炎的目光,愣了下,讪讪地挪开了。
周小雅感觉到肩上传来的温度和力度。那只手很大,指节分明,掌心有粗糙的茧。
她心跳得厉害。
“你……来东莞找工?”她没话找话。
“嗯。”
“有地方住吗?”
“先找制衣厂的江叔。”
“江叔?是不是江福生?振兴制衣厂那个组长?”
林炎低头看她:“你认识?”
“我就是去振兴厂啊!”周小雅眼睛一亮,“江叔是我表舅!他写信让我来的,说厂里缺缝纫工……”
话没说完,公交车一个急刹。
“厚街镇到了!振兴路的下车!”司机扯着嗓子喊。
人群又开始涌动。林炎护着周小雅挤下车,双脚踩在厚厚的尘土上。
天几乎全黑了。路灯还没亮,只有路边大排档的灯泡在风里摇晃,在泥地上投出晃动的光斑。
空气中弥漫着炒菜的油香,辣椒的呛味,还有下水道隐约的酸腐气。
“就是那儿。”周小雅指着不远处一栋五层楼。楼很旧,墙皮剥落,窗户密密麻麻,每个窗口都晾着衣服,像挂满万国旗。
楼门口挂着牌子:振兴制衣厂。
两人走到厂门口。铁门关着,旁边小门开着,门卫室里,一个秃顶老头正就着花生米喝酒。
“找谁?”老头眼皮都不抬。
“我找江福生,江叔。”周小雅凑到窗口,“我是他外甥女,周小雅。”
老头打量她几眼,又看看林炎:“他呢?”
“我朋友,一起找江叔的。”
老头抓起电话拨了个号,叽里咕噜说了几句客家话,然后挂断。
“等着。江组长在车间,马上下来。”
两人退到门外。周小雅把帆布包放在地上,活动了下勒得发红的手指。
林炎靠在墙上,从裤兜里摸出个东西。
是个怀表。铜壳,已经磨损得看不清花纹。他按开表盖,里面没有表盘,只有一张泛黄的照片。
照片上是一对年轻男女。男人穿着中山装,女人穿着旗袍,都笑得温文尔雅。照片背面,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:1980年秋,摄于北京。
这是他被爷爷收养时,身上唯一带着的东西。
“这是什么?”周小雅凑过来看。
“怀表。”
“里面的人……”
“不知道。”林炎合上表盖,“爷爷说我被捡到时,这表就挂在我脖子上。”
周小雅张了张嘴,想问什么,又咽了回去。
这时,厂里走出个中年男人。矮胖,穿着工装,满脸油光。
“小雅!”男人远远招手。
“表舅!”周小雅跑过去。
江福生拍拍她肩膀,目光落到林炎身上,上下打量:“这位是……”
“林炎。江叔,我爷爷让我来找您。”林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。
牛皮纸信封,已经很旧了。江福生接过,就着门卫室的灯光看,脸色渐渐变了。
他抬头,仔细看林炎的脸,又低头看信,反复几次。
“像……真像……”他喃喃自语,把信折好塞回口袋,深吸一口气,“你爷爷……林九叔,身体还好?”
“还好。”
“那就好,那就好……”江福生搓着手,忽然压低声音,“林炎,你爷爷在信里说了,让我给你安排个活儿。但厂里现在……不缺男工。”
他顿了顿,看着林炎的眼睛:“不过,我有个朋友,在镇上的‘好运来’货运站当管事。那边缺搬运工,就是累点,工资还行,一个月能有六百,包住不包吃。你要是愿意,我明天带你去见见?”
林炎点头:“谢江叔。”
“那今晚……”江福生看了看周小雅,“小雅住女工宿舍,八人间,已经打好招呼了。小林你……”
“我随便找个地方。”
“那怎么行!”周小雅急了,“这么晚了,你……”
“有十元店。”林炎说。
江福生想了想,从兜里摸出二十块钱:“这样,往前走过两个路口,有家‘友记’十元店,报我名字,老板能便宜点。明天早上八点,在这儿等我,带你去货运站。”
林炎没接钱:“我有。”
“拿着!”江福生硬塞进他手里,“你爷爷对我有恩,这点钱算什么。”
推辞不过,林炎收下。
周小雅跟着江福生进厂门,一步三回头。铁门快要关上时,她忽然跑回来,从帆布包里掏出个东西,塞进林炎手里。
是个油纸包。
“还是热的。”她脸在昏暗的光里泛着红,“明天……明天见。”
说完扭头跑了。
林炎打开油纸。里面是半个馒头,还是红糖馅的。馒头被掰开的断面,能看到细密的气孔,还冒着微弱的热气。
他咬了一口。
甜味在口腔里漫开。
路灯“啪”地亮了。昏黄的光洒下来,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他抬头看了看天。东莞的夜空被工厂的灯光染成暗红色,看不见星星。
把最后一口馒头吃完,林炎提起蛇皮袋,朝江福生指的方向走去。
走过第一个路口,大排档的喧闹扑面而来。炒菜的火焰在锅里腾起,光着膀子的男人划拳喝酒,穿着短裙的女人踩着高跟鞋走过,留下一阵劣质香水味。
走过第二个路口,果然看见“友记十元店”的招牌。灯箱缺了几个笔画,闪着滋滋的电流声。
推门进去,一股霉味混着脚臭味。
前台,一个秃顶胖子正抱着收音机听粤剧,眼皮都不抬:“住店?一晚十五,押金十块。”
“江福生介绍来的。”
胖子抬眼打量他,咂咂嘴:“老江的人啊……行,一晚十二,押金五块。三楼,307,四人间,已经住了俩。”
林炎数出十七块。
胖子扔过来一把钥匙,钥匙上贴着胶布,写着“307”。
“厕所公用,热水晚上八点到十点。要吃饭出门右转,炒粉五块。”说完又低头听戏。
楼梯很窄,踩上去吱呀作响。墙皮剥落,露出里面的红砖。墙上有各种涂鸦和电话号码,还有斑驳的水渍。
三楼走廊更暗,只有尽头一盏灯,灯泡上积着厚厚的灰。
307的门虚掩着。
推门进去,一股泡面味扑面而来。房间很小,摆着两张上下铺。靠窗的下铺躺着个人,正在看报纸。上铺有个人,背对着门,似乎在睡觉。
“新来的?”下铺的人坐起来。
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,二十出头,穿着洗得发白的确良衬衫,文质彬彬。
“嗯。”林炎把蛇皮袋扔在靠门的下铺。
“我叫陈新材。”眼镜男推了推眼镜,伸出手,“江西人,在电子厂做质检。”
“林炎。”
手刚握住,上铺忽然传来一声巨响——
“砰!”
整个上铺震了震,灰尘簌簌往下落。
然后是一声惨叫:“我!!!”
陈新材和林炎同时抬头。
只见上铺坐起个胖子,一手捂着额头,一手拿着个空泡面碗。碗里剩下的汤汤水水,正顺着他的脸往下淌,流过下巴,滴在脏兮兮的床单上。
“妈的……这破床……”胖子骂骂咧咧,抹了把脸,这才看见下铺站着的林炎。
四目相对。
胖子愣了愣,然后咧嘴笑了,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。
“哟,来新兄弟了?”
他手脚并用从上铺爬下来,光着膀子,一身白花花的肉。肚子圆滚滚,口两团肥肉随着动作晃荡。
“我叫孙健,湖南的。”胖子伸出油腻腻的手,“兄弟怎么称呼?”
“林炎。”
“林炎?好名字!两个火,旺!”孙健用力握手,然后压低声音,“哎,林兄弟,身上有烟没?憋半天了。”
林炎摇头。
“啧。”孙健一脸失望,忽然想起什么,从枕头底下摸出半包“红双喜”,抽出一叼上,又递给林炎,“来一?”
“不抽。”
“不抽烟不喝酒,白在世上走啊兄弟!”孙健自己点上,美美吸了一口,这才发现身上还挂着泡面渣,赶紧拿毛巾擦。
陈新材摇头:“孙健,你又在上铺吃泡面。跟你说多少次了,要掉下来。”
“我哪知道床这么晃!”孙健嘟囔,擦完脸,又凑到林炎身边,“林兄弟,哪来的?找着活儿没?”
“江省。还没。”
“江省?远啊!”孙健一拍大腿,“我跟你讲,这厚街找工作,得找对门路。你看我,在电子厂食堂打菜,一个月四百五,包吃包住!打菜有讲究,手抖一抖,一个月能多挣一百……”
他滔滔不绝讲起“打菜经济学”。
林炎没说话,从蛇皮袋里翻出毛巾和牙刷,准备去洗漱。
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,瓷砖发黄,蹲坑堵塞,散发着浓重的尿味。水龙头滴滴答答漏水,池子里积着褐色水垢。
林炎拧开水龙头,冷水冲在脸上。
镜子很脏,只能模糊照出个人影。他看着镜子里那张年轻的脸,剑眉,高鼻梁,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深。
爷爷说,他长得像他爸。
但他不知道他爸是谁。
擦完脸,他摸出怀表,又看了一眼照片。那对年轻男女依然在微笑,温文尔雅,和他现在这张沾着灰尘和汗水的脸,像是两个世界的人。
“爸,妈……”他低声说,又摇摇头,把表收好。
回到房间,孙健还在叨叨。陈新材已经躺下,就着床头的小台灯看一本《刑法通则》。
“林兄弟,你功夫不错啊。”孙健忽然说。
林炎动作一顿。
“刚才在楼下,你跟老板说话,我看见了。”孙健嘿嘿笑,“你走路,脚跟先着地,脚掌再落下,步子间距都一样。这是练家子的走法。还有你手,指节有茧,虎口尤其厚——练拳的,对吧?”
林炎看了他一眼。
这胖子,眼挺毒。
“小时候跟爷爷学过几手。”他淡淡说。
“何止几手!”孙健一拍大腿,“我看人准得很!你这身板,这眼神,绝对是高手!以后在厚街混,兄弟罩你!我孙健别的不行,就是人脉广,电子厂、制衣厂、玩具厂,哪儿都有我兄弟!”
陈新材从书后抬起头:“孙健,你上个月还说食堂打菜的王师傅是你兄弟,结果人家跟你借五十块钱,你躲了三天。”
“那、那不是手头紧嘛!”孙健脸一红,“这回是真的!林兄弟,我跟你说,这厚街……”
话没说完,楼下忽然传来喧哗。
脚步声咚咚咚上楼,夹杂着骂骂咧咧的声音。
“307!就这间!”
“开门!他妈的开门!”
门被踹了一脚,整个门框都在震。
孙健脸色一变,压低声音:“糟了,是‘白毛鸡’的人……”
陈新材也坐起来,推了推眼镜,脸色发白。
林炎走到门后,透过门缝往外看。
走廊上站着四五个人。为首的是个黄毛——正是下午火车站那个黄毛。他旁边站着个高瘦男人,一头染成白色的头发在昏暗的灯光下很扎眼。
白毛男人嘴里叼着烟,眯着眼。
“里面的人,滚出来。”他说,声音沙哑。
孙健哆哆嗦嗦看向林炎,用口型说:“跑、跑吧……”
林炎没动。
他手放在门把手上,深吸一口气。
然后,拧开锁,拉开门。
小说《南下往事:灰色江湖》试读结束!
 侠客文学
侠客文学